田豐:都說網絡已經無處不在,但其實全球仍有30億人仍未接入互聯網,怎么辦?
田豐:都說網絡已經無處不在,但其實全球仍有30億人仍未接入互聯網,怎么辦?
文章來源: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 | 發布時間:2024-09-11 | 【打印】 【關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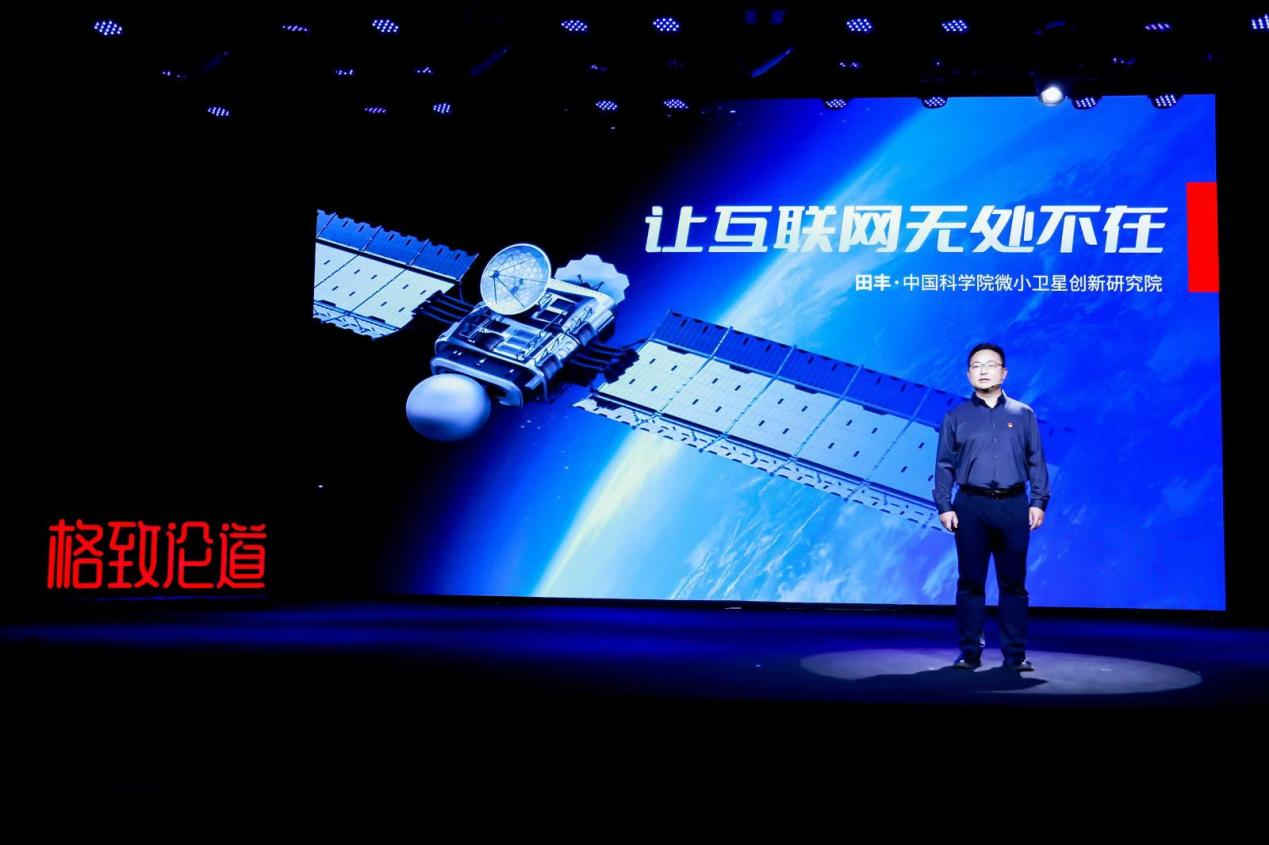
巨型星座將不再是曲高和寡、
高高在上的科研項目,
它將走入大眾的生活中,
成為日常消費品。
大家好,我是田豐,來自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今天我的分享是《讓互聯網無處不在》。
大家看到這個題目可能覺得奇怪,現在的互聯網已經融入到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了啊?為什么還要說讓互聯網無處不在呢?
其實,如果我們離開城市、離開人海,去到荒蕪人煙的地方,就會發現在那里沒有網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更別說去到極地、荒漠等一些更遠的地方了,網絡根本覆蓋不到那里。
目前,我們地面網絡只覆蓋了全球大概10%的面積。而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統計,全球還有30億人口仍未接入互聯網,沒辦法享受互聯網普惠的業務,他們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但互聯網的一個主旨思想就是——讓世界變得更公平。
還有,當我們離地球表面超過1000米的時候,地面基站就很難把信號傳到這么高的位置上了。比如我們坐飛機的時候,每次都會感覺自己有幾個小時和世界斷聯了,沒有任何信號。現在雖然有的大型飛機上有網絡,但那些大部分還是局域網,而不是真正的互聯網。
斷網的感覺非常不好,有時候人們為了上網甚至會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為。比如2020年8月15日,有一艘日本的油輪運行到印度洋島國毛里求斯的時候突然擱淺了,造成了大范圍的原油污染。究其原因,其實是船上有船員想去“蹭網”,所以把船開得離岸非常近。當時正好是一個霧天,所以就擱淺了。大家想想,如果有更便宜、更方便的網絡,這種事情還會發生嗎?
那我們怎么才能讓互聯網無處不在呢?如果只是讓運營商去全球各個地方建站,顯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海上,就沒有辦法去建鐵塔建基站。所以我們有一個很直接的想法,就是把通信設備放在衛星上,打到天上,通過衛星通信給地面和空中提供網絡信號覆蓋.
其實,衛星通信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了,但是大眾一直沒有享受到衛星通信帶來的服務。原因是什么呢?
因為我們原來的衛星通信主要靠的是高軌的同步衛星,這種高軌衛星的信號很容易被大樹和高樓遮擋。另外,高軌衛星運行在赤道上空36000公里的地方,比如我們國家位于北半球,在一些山的北面衛星信號就非常弱,這就是高軌通信的北坡效應。同時,高軌衛星的帶寬也比較窄,所以用高軌衛星提供商業化的互聯網服務比較難落地實現。?
從理論上講,有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就是,在靠近地球的低軌道處,也就是在大概在離地球表面300-1200公里的地方去構建巨型低軌通信衛星星座。這張星座里有數千甚至上萬顆衛星,信號無縫覆蓋全球,不會再有南坡或者北坡效應的問題。
因此,我們希望通過衛星互聯網來讓網絡無處不在。
異想天開還是未來趨勢?已完成:20%?//////////
2014年,我還在上海交通大學讀博士的時候,就有幸參與了國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計劃“空間信息網絡基礎理論與關鍵技術”,這個課題主要就是研究衛星互聯網的一些基礎理論和一些體系架構的知識。?2017年博士畢業之后,我進入了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當時我信心滿滿,想把學到的知識用到衛星上。但那個時候,我們國家的衛星包括國際上的衛星主要還是單星作業,多星組網并非主流的發展方向。?
工作后我參與的第一個項目其實不是通信星座,而是對地遙感星座。我加入了“遙感三十號”衛星團隊,大家可能沒有聽說過我們這個團隊,也對“遙感三十號”知之甚少,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個“三無”團隊。
這個“三無”不是說我們的商品沒有保障、沒有服務、沒有售后,而是無私奉獻、無名英雄、無上光榮。
我今天沒法講這個工作的具體內容,但是通過參與到這個團隊里,我知道了一顆衛星從設計、到集成、再到測試、最終發上天的每一步是怎么走的。也因為參加了這個項目,我從一個學生變成了一個航天工作者,對航天精神和航天人的理解也更具像化了。同時我還感覺到,基礎理論和工程應用之間還是有一段距離的。如果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應用到工程上,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說到衛星互聯網,我們就不得不提到馬斯克。馬斯克在2015年提出了“星鏈”計劃,當時就提出要用4萬多顆衛星覆蓋整個地球,為全球提供網絡服務。但是大家都覺得這個想法太超乎現實了,因為在2015年,全球在太空運行的航天器總量只有1300多個。
而且航天器的造價非常高。一個500公斤左右的衛星造價就是幾千萬人民幣,也就是1000萬美元左右。發射成本也很高,和衛星成本基本上是1∶1的。除此之外,它的生產周期也很長,一顆衛星的生產周期最快要幾個月,慢的話大概要一年甚至是好幾年。
在全球只有1300多顆衛星,同時衛星的制造成本和時間成本都這么高的情況下,很多人都覺得幾萬顆衛星是一個不靠譜的想法。但是,因為我一直是學衛星網絡通信的,從技術層面上講,我覺得用衛星網絡去給全球提供互聯網,肯定是中國航天乃至國際航天發展的一個大趨勢。
?果然,從2019年發射了第一組衛星“一箭60星”,到2024年4月為止,馬斯克的“星鏈”(StarLink)在軌衛星已經有6800多顆了。而且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從2019年到2024年差不多5年之內,它已經迭代了五六個版本,從0.9版本到了現在2.0的mini版本。更重要的是,它已經實現了全球230萬個衛星終端,開始去盈利了,實現了收支平衡。除民用之外,眾所眾知,星鏈也有重要的軍用潛力,比如在烏克蘭沖突上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先從試驗衛星開始已完成:40%?//////////
因此,我們國家從2017年開始,也慢慢嘗試著去建設我們自己的衛星互聯網。我們中國科學院和上海市科委聯合投資的低軌試驗衛星就是做這個的。
低軌試驗衛星主要是試驗什么呢?巨型衛星互聯網其實和地面互聯網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它的系統架構和地面的互聯網是不一樣的。
地面的移動互聯網有很多種基站,有5G基站、4G基站,有大的基站,也有我們室內毫米波的小基站,還有Wi-Fi熱點。但是這些基站有一個共性——它們都是固定在一個地方的。用戶無論是用電腦、用手機還是其他設備終端,它們之間的運動速度相對來說都比較小,基本上很長時間都是連著同一個基站的。即使運動那也是因為我們人動了,才帶來了基站的切換,切換規模總體上比較小。
但是低軌衛星不一樣。假如低軌衛星的軌道高度是1000公里,它的運行速度就會達到每秒7公里左右。基站也會隨著衛星運動,這也就意味著通信的時候,如果過頂的衛星超出視距,就沒辦法通信了,需要經常切換。衛星在經過正頭頂的時候通信時間會長一些,能達到11-12分鐘,其他情況下的通信時間會更短,總的來看一顆衛星持續通信的時間可能只有6-12分鐘。?
那么,如何解決這種衛星快速運動帶來的大規模的終端切換呢?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用多星多波束協同接力通信。以圖中為例,隨著衛星的運動,這顆紫色的衛星馬上就會切換到這顆綠色的衛星的位置,代替它去覆蓋它的用戶。也就是說每顆衛星都有點波束去對終端進行接力式服務,同時衛星之間也需要開展通信,保證服務不中斷。
這是我們發射的兩顆試驗衛星,主要用來驗證我們的系統架構以及星間鏈路的通信。這顆衛星搭載了我們跳波束通信載荷,單顆衛星可以通過波束的捷變去為多個終端服務。同時,兩顆衛星之間又有星間的激光鏈路,這也是我們國內首次實現雙星在軌和地面10Gbps組網的驗證。
之所以選用點波束,是因為它的波束的頻段非常高,是20GHz左右。它的雨衰(無線電波進入雨層中引起的衰減)也非常大。如果我們用一個很寬的波束,它的衰減會更大,傳輸速率就比較低。我們把能量聚焦到一個點波束,就能提升它的服務需求。當然,說是點波束,在地球上的覆蓋范圍依然很大,有大概100公里左右,足以覆蓋北京市或者上海市這么大的范圍。
衛星打上去之后就需要去測試,當時我們開始測試的時候正好是8月份。上海的8月份非常炎熱,而且還很悶,正好還是放高溫假的時候,我們就一起跑到單位的樓頂做測試。
測試的時候,因為衛星的軌道高度低,運動速度快,所以過境時間很短,不是每天每時每刻都能在我們頭頂上。有時候在中午的12點過境,有時候在晚上的12點,一天過境3-6次。這就需要我們拋開自己的作息時間,完全去跟著衛星轉。
整個高溫假結束之后我發現,雖然我們并沒有出去旅游,但是皮膚比出去旅游的同事曬得還黑,連頭頂都曬黑了。但是測通之后,我們還是很有成就感的。
突破衛星互聯網的核心技術已完成:60%?//////////
可是,雖然這兩顆衛星已經能夠通信了,但是還遠遠做不到商業化。因為任何一個用戶都不希望自己在接入互聯網后只通信個幾分鐘就斷了,然后等待很長時間再通信幾分鐘再斷掉。這樣的衛星互聯網是推廣不開的,所以我們要建設一個巨型的星座。
建設巨型星座和我們傳統的衛星星座是不一樣的,它的規模是原來幾顆星的星座的好幾萬倍。因此,我們不能用傳統的衛星制造模式,讓總體單位和外協單位共同去做。我們必須把從頂層的系統設計到底層的核心網絡單機全部打通,這樣才能把系統做到最優,把單機成本做到最優。以此來支撐后續一年發射幾百顆最終達到幾千顆、上萬顆衛星的在軌驗證。只有這樣,才能把這個巨型星座做起來,使它不再是曲高和寡、高高在上的科研項目,而將走入大眾的生活中成為日常消費品。
于是,我就從原來的系統架構轉而研制底層的空間網絡單機。其中研制的第一個單機就是路由器。
路由器分為數據轉發面和控制處理面兩部分。地面路由器的數據轉發面所用的芯片已經商業化了,但是這些商業化的芯片卻不能直接用在天上,因為天上有很多不確定的環境。
而且還有很多單粒子,這些高能粒子打進來之后會把我們的邏輯芯片打反轉。邏輯芯片里儲存的都是0和1,它會把1打成0,把0打成1,造成單粒子反轉。所以我們很難簡單地用商業化的芯片去搭建空中路由器的數據轉發面。
控制處理面相對來說要簡單一些。因為控制面的數據速率并不高。那么我們就可以用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現場可編程門陣列)去做一些宇航防護、三模冗余,開發我們空中路由器的數據面。
在開發過程中,交換速率和交換端口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為星間通信速率是10G,如果有4個端口的話,就能進40G、出40G,通信速率達到80G。因此,我們就用了交換矩陣的思想,在衛星上搭了一個高速交換、支持多個端口、多檔速率的交換架構,來解決交換速率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路由器和路由器之間需要連通。地面的網絡一般都是用光纖連通,但在衛星上很難用光纖,因為在太空拉光纖肯定是不現實的。于是,我們就使用了星間激光通信,也就是用激光鏈路來組網通信的方式。
我們的試驗衛星上就有星間的激光通信,在軌也驗證這種通信成功了。但是同時,我們也發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太陽光干擾。我們的激光通信用的是850納米波長的光,但是太陽光是全頻段的,它打到激光器的接收端之后會干擾我們,這個叫日凌干擾。還有就是單粒子的干擾,以及負載突然加上來之后也會對激光終端產生影響。
在不穩定的鏈路中,我們要把網絡做成可用的,就得結合激光終端和路由器,把它們聯合起來做優化。這就要求我們不但有系統設計,還要有底層的、核心的空間網絡單機。無論是軟件、代碼還是硬件的架構,這些東西我們都要設計出來,才能讓它真正落地。
用互聯網的思維做衛星已完成:80%?//////////
巨型星座的規模非常大,傳統的這種花好長時間好多錢去做一顆衛星的思路肯定是不行的,我們要用低成本但是高可靠的空間網絡單機去搭建我們的衛星互聯網。
那我們怎么去做驗證呢?航天跟地面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一定要在軌驗證。我們也是借鑒了互聯網的思維,快速迭代、快速驗證、快速型譜化。馬斯克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于是我們中國科學院就創立了創新X系列衛星,它沒有明確地說要在軌完成某一個特定的任務,而是大家眾籌起來的。比如“創新X-01星”搭載了十幾個載荷,這些載荷來自我們中國科學院和多家高校單位。后續我們還會形成航班化發射,一年7顆衛星,每顆衛星上搭載二十幾個載荷,形成低成本空間試驗的新范式。也歡迎有需求的單位跟我們多聯系,把新技術通過這個平臺發射上去。
需要說明的是,搭載“創新X-01星”的火箭是“力箭一號”。“力箭一號”是我們中國科學院自己研制的火箭,現在的生產力也能支撐航班化發射的計劃。
當然,衛星的迭代速度會越來越快。如果在軌驗證的速度還是不能滿足,那我們的迭代速度還能怎么突破呢?
我們成立了衛星數字化技術重點實驗室,搭建了數字孿生衛星網絡。
在數字孿生衛星網絡里面,衛星的運行、功能、性能以及運行環境和真實的衛星是一模一樣的。我們可以通過采集衛星上的一些真實數據,結合數字孿生網絡里豐富的測試數據,來迭代下一代的網絡、路由器和激光終端,以此加快我們的速度。
最終,我們的空間網絡設備將采用模塊化設計。每一個單板都會形成路由、存儲、星間通信、星地通信等各個功能。可以根據不同型號的需求加快迭代,來做到系統的最優。
同時,我們也建立了批生產產線,包括貼片、自動化測試和集加工等等,實現了空間網絡設備的批量化生產。在單機批量化生產之后,后續整機的組裝也會做到批量化。
現在,中國衛星互聯網已經成為蓄勢待發。我相信在未來它會帶動、輻射很多產業的協同發展,比如遠洋旅游、遠洋貨輪、飛機互聯網等都會跟衛星關聯。當整個地球的互聯網全部打通之后,我們的思想就會達到更遠的地方。
?這個行業充滿了無限機遇,期待大家多多關注。最后打個廣告,我們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目前形成了從系統設計到衛星集成,再到單機研制的全流程的創新性平臺,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特別是歡迎大家報考我的研究生,我是田豐。謝謝大家!
文章來源于格致論道講壇,作者田豐
